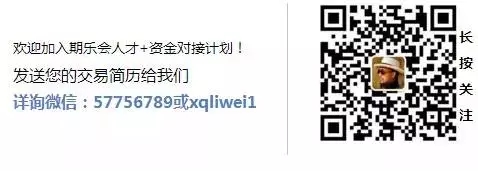
从“尚武精神”到“妇女态”
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人个个强悍好战,连吴越地区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,先后出现吴王阖闾、越王勾践两位霸主。再如,楚国以军事立国,举国上下有一种喜征战、重成败的尚武习俗。楚康王即位后,五年没有率师出征,就认为自己是莫大的失职,死后无脸见祖宗。同样,秦国在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中一直处于优势,这也与其长期以来形成的尚武习俗分不开。
那时,人民对于勇武之士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,相反,懦弱、胆怯遭人鄙夷。不论男女,皆以高大健硕为美;侠客遍地,武士横行。至夏商周三代,虽已强调礼乐教化,却仍然重视武备。讲求文武并重,即所谓“六艺”: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其中的“射、御”就是旨在培养保卫国土的武备之才。
然而,到了明朝万历年间,传教士利玛窦在信中却这样写道:“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。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,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,相互殴斗时揪头发。”
清初思想家颜元曾痛骂道:“宋元来儒者习成妇女态”,全国成了一个放大的禁宫,绝大多数人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,望眼欲穿、苦心孤诣地等着权力的临幸。
颜元说:“衣冠文士羞于武夫齿,秀才挟弓矢出,乡人皆惊,甚至子弟骑射武装,父兄便以不才目之”,他深切地述说道:“无事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,即为上品矣!”,并认为中国人变文弱的病根就是“千余年来,率天下人人故纸中,耗尽身心气力,作弱人、病人、无用人者,皆晦庵(朱熹)为之也”。
从“侠客”到“罪民”
春秋时代,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。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里记载了好多刺客侠士的事迹,其中,专诸、聂政、豫让、荆轲,“四大刺客”尤为著名,他们的信条无不是“士为知己者死”,以视死如归的气魄和撼动山河的壮举,让自己的侠义之名万古流芳。
侠人义士救危扶困,济人不赡;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;知恩必报,赴火蹈刃;受人之托,一诺千金。赵氏孤儿、鱼腹藏剑、聂政刺侠累、荆轲刺秦王,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,演绎了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,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、生死相许。春秋时代的侠客,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。他们行侠仗义,不是为利,甚至不是为名,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。
及至明清,“侠客”们却自愿攀附权力,沦为权力的附庸。《三侠五义》中的侠客个个自称“罪民”,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。如鲁迅所说,春秋时的侠客,是以“死”为终极目的,而明清小说中的侠客,却个个成了地主的官僚,游走于黑白两道,失掉了“侠义”的原则本质,变得市侩和功利。
从“刚健清新”到“形如槁木”
被封建统治阶级做为统治工具的“孔孟之道”,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,而是有着刚健清新的一面。春秋士人大都是理想主义者,他们不迷信权威,也没有思想禁区,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,将自己所学之“道”凌驾于权势之上。合则留,不合则去。这一点,以儒家最为突出。
等到秦始皇统一六国,各国的知识分子只能生活在一个皇帝之下,没有了选择的机会,也没有逃亡的自由,只能为这一个政权服务。秦始皇确立了君主制,给专制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到后面的历朝历代,继续在专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。
秦汉以下,虽然在世俗层面,士人们遵守权力秩序,但是在精神层面,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“圣人”自我期许,追求“始乎为士,终乎为圣人”,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。
但到了明清,儒生出身的大臣们已被驯化得“百炼钢成绕指柔”。在皇帝明察之下,他们老老实实,卖命效力,以图飞黄腾达。皇帝一旦放松警惕,他们就会大肆贪污,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。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。所谓操守、尊严和人格,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不着边际的空话。
宋代以前的中国人,称得上伟大,说自己想说,想自己所想,生机勃勃,生趣盎然。宋代以后的中国人,不但失去了创造力,也失去了感受力。从上到下,人们既狡猾又愚昧,既贪婪又懦弱。
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黄河,先秦是上游,清澈见底;汉唐是中游,虽泥沙俱下,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。明清是下游,已干涸萎缩、奄奄一息了。
虽然明清曾出现过“万历中兴”“康乾盛世”,但社会僵化已病入骨髓。德国著名哲学家赫尔德,说道:“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,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,描画有象形文字,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;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,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。”
“奴隶性格”和“专制性格”
中国人最早的性格改变要从秦朝说起。秦国自立国之初,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,长期与戎狄杂处,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。草原文化中没有民主观念,没有权利意识,以绝对服从为天职,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
进入春秋末期,此时中原社会已经变得比较柔软,比较有宽容度,崇尚优雅和尊严。但是秦国不同。在战国七雄中,秦国文化是最野蛮、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。
商鞅变法从军爵制度开始,取消贵族世袭,有军功战绩,才能够重配爵序。商鞅采取“愚民政策”,把文人、商人、工匠视为“国害”。他在渭河边论法,一次性就屠杀了700多反对他执政路线的文人。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,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“虎狼之国”。但最终还是野蛮战胜了文明,秦国击败六国,统一了天下。
皇权的产生,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,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。此后的两千年间,中国社会万马齐喑,死气沉沉,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,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。
中国人一直在“做稳了奴隶”和“想做奴隶而不得”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,“奴隶性格”和“专制性格”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。
从“雍容大气”到“内敛文弱”
凡是唐代的事物,无一不博大恢宏,健硕丰盛。唐代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,气势不凡,雍容华贵。唐人喜欢画骏马、苍鹰和牡丹;宋代的文人画家却偏爱画梅兰竹菊,它们独处山中,低调含蓄,幽冷寂寞。唐朝有壮丽无比的诗句:“秦时明月汉时关,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,不教胡马渡阴山”;而北宋范仲淹的“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,羌管悠悠霜满地”,读起来是那么的凄凉。
究其原因,在于宋代统治者对武器的恐惧。以兵变夺得江山的赵匡胤不想再被自己的部将所推翻,开国不久,他便以“杯酒释兵权”,戏剧性地解除了最有实力的将军的军权。在制度的方方面面限制武将的权力,降低武官的地位。赵匡胤还颁布了禁止武器的法令。可笑到,连民间祭祀、社戏所用的仪仗刀枪也被禁止。
除了对武将大力防范,赵匡胤也没忘记给文臣套上辔头。运用分权和制衡之术,消除了文臣在制度上对皇权形成威胁的可能。把宰相大权分割成几块:兵权交给枢密院,部分行政权交给新设立的“参知政事”,“三司”专管财政,分掉了宰相的财权。诸如此类等等。
在专制集权的方向上,继秦朝之后,宋朝实现了专制政治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升级。这种政治设计,大幅度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。
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驰骋疆场为荣。宋代男人开始失去了尚武精神,他们沉醉在案头书牍之中,在日复一日的浅吟低唱中把时光送走。宋人性格也越来越细腻。正如梁启超所说:“重文轻武之习既成,于是武事废坠,民气柔靡……奄奄如病夫,冉冉如弱女,温温如菩萨,敢敢如驯羊。”
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。宋朝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皇位的安全,却导致整个民族陷入危机。虽然宋代社会发展较有成就,人民生活相对安定,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、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,却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。
从“失魂落魄”到“卑污暴戾”
如果说宋朝使国民气质上变得更文弱,那么元朝则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。在元代,上层文化遭遇到了毁灭性打击,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,成为主流。忽必烈就曾置疑:“汉人惟务课赋吟诗,将何用焉?”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,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,始终不予重视。有学者曾说:“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,并且凌辱和消磨了他们自己的灵魂。”
自古华夏和蛮夷的族群之别很强盛,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。南宋军队虽称软弱,但也涌现了众多铮铮铁骨。襄阳之围,宋人坚守了5年;常州之战,数千守军战斗至死,只余六人,反背相柱,杀敌多人方壮烈殉国;扬州之围,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,“城中粮尽,有自食其子以坚持者”。
数十年的抗元战争,那些有血性、有骨气、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屠戮。有人说,在文天祥赋诗而死、陆秀夫负幼主蹈海而亡后,中国作为一个文化体已经灭亡,“崖山之后,已无中华”。中国文化受到毁灭性的打击,中国的脊梁已被打断,中华精神也已经灭绝。
及至明朝,国民性又开始染上了“流氓气”。其上层政治流氓统治术,核心是十六个字:“不讲规则,没有底线,欺软怕硬,不择手段。”这一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,然而蔓延迅速,拥有极强的生命力。
朱元璋为禁止官吏们过度剥削,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:“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,也等长成然后用……”
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,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,把这些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,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。因此,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,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,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强硬。
士人想做隐士的自由首次在明朝被剥夺。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,“率土之滨,莫非王臣。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,是自外其教者,诛其身而没其家,不为之过。”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拇指剁去,以示不肯出山做官,被朱元璋“枭令(砍头示众),籍没(登记并没收家产)其家”。中国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人格的空间。
明朝统治,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,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,禁止海上贸易,闭关锁国,对内则是全面社会控制。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,各级官员都是狱卒,所有百姓都是囚犯。百姓稍有违规,便“充军”“斩首”“乱棍打死”……
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,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:“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,自足乎一世之间;守道循礼者,不免于饥寒之患。”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,他们相信:“强中更有强中手,恶人须服恶人磨”。
《水浒传》人物的卑污、暴戾是元明时代中国人性格的真实写照。
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,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。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,造假之风大兴。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,成为中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“奴性”
1793年,正值清朝乾隆年间,来中国造访的英国外交团长马戛尔尼,彻底打破了莱布尼茨、伏尔泰此前对中国的想象。
英国人在菲律宾群岛、今天的雅加达、槟榔屿等地方看到的中国人,活泼自然,聪明有创造力,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,缺乏自尊心,是胆小、冷漠、自私、麻木和残酷的。
他们的记录中写道:“中国普通百姓外表非常拘谨,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。在他们私下生活中,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。但一见了官,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。”
“在这样的国度里,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,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个点头而挨板子,还要被迫亲吻打他们的板子、鞭子或类似的玩意……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。”
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,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,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、最完善、最牢固的专制统治,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,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、加固、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。
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,对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,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,变为一具僵尸。人人自称“奴才”,个个犹如行尸走肉。
雍正皇帝在《朋党论》中说:“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,所恶者恶之,是非画一,则不敢结党矣。”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:“奸臣”固然并非国家幸事,“名臣”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。他说:“乾纲在上,不致朝廷有名臣、奸臣,亦社稷之福耳。”
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,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,打造了一个清代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(yú)的铁打江山。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,就是:“前代所以亡国者,曰强藩,曰权臣,曰外戚,曰女谒,曰宦寺,曰奸臣,曰佞幸,今皆无一仿佛者。”
反思
秦始皇以后,中国的皇朝历史也是不断演进发展变化的,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权专制和统治技术,发展越来越精微,越来越牢不可破。它已经渗透、融化在国民性当中。
从梁启超到鲁迅甚至毛泽东,都有过试图改造中国人思想的理论和实践。但改造了一百年,我们整个民族的素质似乎变化甚微。
2011年在佛山,一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孩相继被两车碾压,7分钟内,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,漠然而去。最终,一名拾荒阿姨上前施以援手。
不同制度背景,对民众的素质有决定性影响。在制度建设没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,期待国民性的彻底改造是不可能的。
坏的制度可以激发人性中恶的成分,使人性更为扭曲,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;好的制度固然不能使坏人变好人,但至少可以限制坏人,使之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。
来源:张宏杰/著《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》 转自儒风大家(微信ID:rufengdajia)
